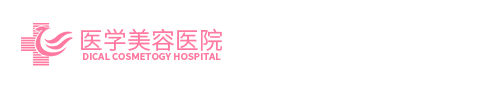新闻资讯

分组完成后,就是拼接。“一件玉器的内环和外环可能都有残缺,我们在拼接前要先估计它对应的大小规格,这需要丰富的经验。”南京博物馆修复人员余子骅拿出一个圆环,“然后我们会找到一个类似这样的卷型器,把玉器的外壁先固定,再计算出玉器的内径,专门订制一个木楔那样的工具。把内外都卡住以后,把一块块碎片慢慢地放进去,花大量的时间慢慢调整,直到完全成一个玉器的形状,再仔细粘接,达成你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效果。整体上,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。”
接手玉棺后,由于玉棺坍塌、叠压在一起,加上盗墓者的破坏、盗扰,虽然相对位置还在,但依然对接下来的修复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信息,除了拍照、绘图的记录方式外,赵晓伟团队还做了 3 D扫描,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残缺、破损的现状保存在下来。扫描完以后,赵晓伟团队先后跟陕西师范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合作,对漆、金属(金银片)、青铜、玉器等相关工艺和成分进行检测和研究, 2013 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清理工作从玉棺西侧板是残存情况最明确的,保存现状也是相对最完整的一个部位开始,先是揭取玉片,玉片揭取完之后,可以看到镶贴玉片的漆灰层(腻子),揭开漆灰层以后,可以看到残存的梓木棺板。放在地下两千多年,棺板木胎可以说糟朽殆尽了。腐朽后的空隙全部被墓室内的白膏泥填充了。从白膏泥破裂的间隙,赵晓伟发现有从底部(玉棺外侧)伸进来的白色玉片,这和棺内发现的玉片整体呈青绿色的截然不同,这也引发了团队的疑问,这是掉落在棺外的玉片腐蚀白花了,还是是玉棺外面也镶玉?
这具玉棺总体是朝外侧倒塌的,那么西侧板外面的漆皮一定是相对完整的。为了不破坏其整体性,以及为了保障更多信息的原始性,赵晓伟团队采用了脆弱遗迹的提取技术,也就是薄荷醇加固法,先把薄荷醇熔融以后涂上去,再铺上纱布,就像揭壁画一样,作为一个整体提取下来。因为加固面积较大,长 2 米、宽 0.4 米, 5 个人通力协作,成功将其提取并翻转过来。看到的情形是相当令人欣喜的,玉棺西侧板外侧残存的漆皮大体是保存完好的,棺外的装饰一目了然,有小铺首,有玉璧,有玉璜,有玉龙——现在看来应该是犀形的玉饰。除了装饰性构件,漆皮上能辨识出的彩绘纹饰,也异常精美。
在这期间,许多事情也在同时推进。比如说,推理复原研究的时候可以只讲形制、结构、装饰风格,但落实到具体制作层面,就不能不追求精确了。到设定棺身的长短尺寸时,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决定,因为这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:一是玉片,棺盖、棺体镶贴玉片总共涉及到了 10 个面,这些材料形成图案的尺寸,能不能都跟棺体对应上;二是棺木胎的厚度,以及各个棺板之间的组合方式;三是新做的木胎还需跟残存的铜扣边的尺寸相对应。古人为棺盖、棺体设计了铜扣边。铜扣边主要有两个作用,一是加固,二是装饰。最终测算下来,这个玉棺长 2.12 米,宽 0.64 米,棺板有多厚呢?
在一次对残存漆皮进行清洗时,偶然发现漆皮背面有木质纹理,修复师就从该纹理入手:古代棺板是靠榫卯结合起来的,两块板子相互拼接,木头虽然烂了,但纹理还存在,刚好能找到部分纵向的纹理和横向的纹理,还保留了个别榫卯的遗迹。经过测量,边缘处所呈现的纵向纹理约 3 厘米左右,也就证明棺的木胎是 3 厘米。木胎厚度确定后,接下来就是要把棺盖、棺体木胎共 10 个板面的以及榫卯的位置、尺寸确定下来。这个过程是非常纠结的,甚至“抠”到了两三毫米,尽管如此,实际制作的漆棺做出来还是有误差的,但不影响大局。
修复的重中之重是玉片的制作。一直到 4 月份,赵晓伟还没有找到古人设计装饰的原理,只是机械地复制,用雪弗板制作模型片,互为补充,放在缺失的地方,但看上去总是不协调,一度陷入僵局。其实,古人在制作玉棺时也要进行设计,除了玉璧和柿蒂形玉片之外,几乎每个玉片都有编号,也就是说,古人在设计和制作玉片的时候,也担心弄混了,所以要编号。西侧板玉片背面都标有数字,没有前缀,东侧板则在编号前加了一个“方”字,底板是“下”字,盖板是“上”字。赵晓伟说:“我们在机械复制的结果看起来是差不多的,但总归没有完全对应上,不是这里大了就是那里有偏差,反复折腾,最后所有人都搞得不胜其烦了。”
折腾了很久之后,自然会有灵感闪现。有一天赵晓伟团队发现,在一个玉璧的两侧有两个小三角,编号数是一样的,比方说,一个小三角编号是 53 ,另一个小三角编号也是 53 ,但出土的时候确实就在玉璧的两边,间隔开了。一开始团队怀疑是不是古人编重了。不知怎么,灵感突现,团队猜想它们是不是本来应该属于某一个单元的,后来被玉璧打断了,所以依然保留着两个编号这样原始的状态。在这种想法的引领下,赵晓伟团队就尝试在西侧板的基础上继续研究。在残存的玉片中,除了玉璧和柿蒂形玉片,整体风格是呈现出三角形和菱形,以及所谓的异形片——往往出现在玉璧的旁边。
在完成了玉片的修复工作后,赵晓伟团队投入到棺外的彩绘工作。东侧板经过清洗、整理,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电脑绘图。如残存彩绘神兽的头也算一种动物,残存的爪子也算一种动物,总计大概有 40 多个个体,其中西侧板和北挡板的彩绘加起来也就 15 个神兽。反而是原先不报希望的东侧板提供了非常丰富、非常生动的神兽纹饰。尽管是一堆碎片,但根据云纹线条的走向、几何纹的走向,团队还是把东侧板的构图还原出来了,其精彩程度不亚于西侧板,尤其是经过拼接后,东侧板还有一个完整的玉璜。
很有意思的是,东西侧板的犀形玉饰(之前叫玉龙)看似形状一样,其实大小略有区别,也不属于一个个体——就是说,这具玉棺所有装饰用玉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生活中已有的玉器。古代也是讲究节省的,毕竟玉是很珍稀的,得充分利用,所以很多玉片都是对剖过的——把旧有的玉片平分,甚至有一个三角形的玉片,长只有 8 厘米,没剖成功,可是又舍不得扔,就粘合在一起,然后贴到棺里。这不仅说明玉在当时极其珍贵,也反映了汉代玉工极高的治玉技术。
在修补玉器的过程中,首先是用生漆和面粉调制黏合剂将破损的碎玉黏结起来,玉的断面如果有明显的空隙,在修复前还要适度打磨并刷上隔离胶。接下来在破碎的玉片断面上均匀地抹上,然后将碎片准确地黏结在一起。待基础层干透后,再反复地填补漆灰直到塑形完成,一旦所有修补部位的形打磨塑造完毕,用生漆髹涂两至三遍,确保所有的细小的凹陷处都填补完整,漆底坚固光滑。这时候就可以做上金的工序了,在贴金的位置涂金胶漆,为了保留玉器内敛、温润的美感,用太粗的线条会破坏玉壁整体的气质,所以需要用很细的线来描绘,线条虽细,但不弱,待金胶漆将干未于之时进行贴金,贴金的时候用蚕丝球蘸少量金粉轻柔地扫涂在金胶漆上,反复擦拭,金面会呈现光泽,等两三天彻底于固以后再擦漆保护金面,增强金面的耐磨程度。用金缮修补的玉器就完成了。
另一种以金为材料修复破损玉器的工艺是金镶玉工艺,金镶玉是一种镀金工艺,在器物表面镶锡包金,设计比较多样,灵活多面。从对玉的损坏程度来说,金镶玉工艺较为复杂,稍有不慎则会损伤玉器,而金缮工艺以大漆作为黏合剂将碎玉粘合,以金箔、金粉修缮之,让破损的玉器得以重新幻彩。从效果来看,金缮修复过程中,如果技法采用得当、优质,在还原破损的器物的同时,还能增添一种别样的“残缺之美”。且大漆黏性大、稳定性强、纯天然没有化学污染,能达到更好的修缮效果。
在玉器修复中,金缮工艺是工匠审美与残器气韵的高度结合,具体来说,玉器的造型、种类、功能与装饰影响着人们对器物的整体感受,金缮工艺在玉器修复中的装饰性也是它的重要特性,线面结合是金缮工艺中常见的表现手法,线条极具节奏和韵律,精致似克林姆特的画作。例如,金缮修复师邓彬的金缮汉代玉石剑首作品,修缮师采用的技法、材质、纹样等与器物高度融合,赋予原器物新的气韵的同时,也保留了玉本有的温润和自然,还带有一丝庄重之感,处处体现着作者的匠心巧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