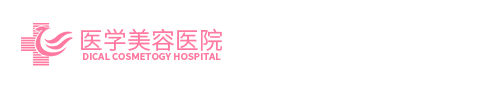新闻资讯

2022年,一本名为《谈心: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》的书,在中国内地、香港、台湾同时出版,作者金圣华,写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谊,以及彼此间关于阅读、写作、生活的心得体会。坊间肯定更熟悉明星,但在翻译领域,金圣华是学术界的名教授,远非“明星”可比。金圣华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,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系教授、荣誉院士及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,另一社会职务是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、荣誉会士。金圣华曾两度担任香港翻译学会的会长,为推动香港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。
查阅文献,关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,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1971年10月6日,‘香港翻译学会有限公司’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。七个月前,七位会员Louis Cha,T. C. Lai,Meng Ma,Stephen C. Soong,Alex H-H Sun,Philip S. Y. Sun和Siu-Kit Wong作为发起人,召开成立大会,旨在香港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,以促进与中文翻译有关的标准、交流、出版和研究。这些发起人,包括六位杰出学者和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兼报纸出版家,他们秉持的坚定信念,铭刻于学会章程中。”
1944年,金庸二十岁,因有游历外国的想法,遂产生了当外交官的理想,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。中央政治学校是“党立的最高学府”,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。这年上半年,大一学期结束,金庸的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,但到了秋天,他却不得不离开学校。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严家炎教授说:“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,那个学校控制很严,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‘异党分子’,甚至还乱打人。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,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。”
失学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蒋复璁。蒋复璁是海宁硖石人,军事家蒋百里的侄子,1940年,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首任馆长。通过蒋复璁的关系,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工作,名义是干事,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,上班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。这份工作薪水不高,仅够糊口,但在管理图书的同时,给了年轻的金庸一个大量阅读的机会,他集中读了大量西方小说,包括英文原著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(今译《艾凡赫》),并英法文互参读了《侠隐记》(今译《三个火枪手》)、《基度山恩仇记》(今译《基督山伯爵》)。
金庸对读者市场的需求极为敏锐。1939年12月,他十五岁,因同学张凤来、马胡蓥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,但找不到合适的参考书,于是搜集材料给他们作为参考。在此基础上,金庸编辑了《献给投考初中者》一书,于1940年5月出版,这是他的第一本书,问世一年,印刷20次,销量10万册,带来了丰厚的报酬,直到1949年3月,南光书店还在出版《献给投考初中者》,可见此书的长销程度。金庸若干年后回忆往事,对池田大作说:“我创办《明报》而得到成功,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。”
一期杂志需要的内容不少,作为新刊,稿源是个问题,但是从创刊号目录上的13篇文章来看,有《齐格菲防线大战记》《意大利投降内幕》这样关注世界战事的译文,也有《飞弹之谜》《最近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》的科普文章,还有文学类的《少年彼得的烦恼》《安娜与星罗王》等小说、散文等,做到了普遍满足读者的需要。金庸还以笔名“查理”发表了长篇小说《如花年华》首章,占了7页,约有9000字,这或许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可惜未完。
杂志中的文章以译文为主,目录上的译者除了“查理”,还有段一象、良莹、张捷、贾鼎治、王人秋、俞淬、马玮等。这其中,贾鼎治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,1925年出生,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,当时年少,正在重庆。其他翻译者的名字无从可考,考虑到金庸在中央图书馆的便利条件,以及出刊的紧迫时间,推测这些翻译者大多是金庸自己,他为了让读者感觉本刊实力强大,供稿者甚众,换了不同的“马甲”,《太平洋杂志》可称金庸最早的“译文集”。金庸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丰富资料,每天得空就翻译,下班后,又带着《英汉词典》,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,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。他以查理为笔名,在“发刊词”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——传播知识,传播真、善、美:
金庸翻译的《基度山伯爵》计划出版多少册,无从可考,但第一册售价250元,价格不菲。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,金庸的月薪仅有50元左右。抗战时期,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通胀,重庆物价到抗战后期上涨了1560多倍。居住在重庆的老舍曾回忆,起初四川的东西便宜,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,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”,但从1940年起,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涨。作家张恨水提到他初到重庆时肉价两角一斤,五年后肉价暴涨到三四十元一斤,他要同时创作七部小说,写小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发表散文、杂文、评论等,以换取稿费养活一家人。
湖南大学于1938年内迁至辰溪县,距离农场不远,金庸便想借读湖大,重续学业,于1945年8月8日,写信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:“学生原籍浙江海宁……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……如蒙允许,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,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,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,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……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,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、情况之艰苦,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……”并备言自己为了求学,千里辗转,突破日军防线的艰辛经历。金庸言辞虽切,但校方未予通融,胡庶华校长于18日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:“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,本校不能直接收容。”回绝了金庸的请求。
金庸后来在和池田大作对谈时说:“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,最初是在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。”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于1927年3月12日创刊,1937年2月1日社址迁至杭州众安桥畔,大楼五层,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。《东南日报》是浙江地区有名大报,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浙江日报社。不过进入东南日报社的时间,金庸记忆有误。浙江档案馆馆藏有东南日报社的全宗档案,其中有职工登记表、金庸签下的“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”以及离开报社时的“辞呈”。按照职工登记表记载,他进社日期是“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”,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,介绍人是陈向平。
陈向平接信后,向杭州《东南日报》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。汪远涵是浙江温州人,毕业于复旦大学,1939年和陈向平一同进入《东南日报》工作,从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。金庸初到编辑部,说是外勤记者,汪远涵给他安排的任务却是“翻译”,按“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”上提供的说法“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,工作服务期内,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,听从调度,谨慎奉公……”这份工作实则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英语广播,选择可用的翻译。金庸偶尔也会翻译一些英文报纸上的短文,以备报纸缺稿时使用。报社没有录音设备,这种国际新闻稿全靠直接收听后翻译,金庸晚上八点开始工作,边听边记,最后凭借记忆全文译出。
进入《东南日报》不久,1946年12月5日,金庸即在《东南日报》第三版上发表《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——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》,这是金庸翻译伦敦《》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,署名“查良镛”。金庸出色的翻译水平,给汪远涵留下很好的印象。1988年,汪远涵与金庸通信时还提到这件事,印象深刻:“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来杭,做这份收听和翻译的工作……陈向平询问过你在《东南日报》的境况,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,行文流利,下笔似不假思索,翻译特好。”
1947年的六七月间,上海的《大公报》公开招聘三名翻译,金庸看到消息后报了名。当时《大公报》在新闻界如日中天,待遇高、收入稳定,因此应聘人数达到109名。《大公报》最后选了10人进入笔试,金庸幸运位列其中。笔试试题由《大公报》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,并最终由他阅卷打分。“试题英文电报一,社论一,译为中文。”金庸只用了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,随后,他顺利通过了口试。不得不说,金庸的翻译功底和《东南日报》的报业经历起了关键作用,他成为第一个被录用者。
当时金庸的堂兄查良鉴任上海市法院院长,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,通过这层关系,以及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,金庸在上海停留期间,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,继续未完成的大学学业。10月6日,金庸以此为由,向东南日报社申请“准予赐请长假”,“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”。第一次的报告批有“慰留”字样,他于同日再次递交申请,眼见他去意已定,报社“勉予照准”。10月底,金庸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工作。
《时与潮》杂志专门报导国际问题,也评论国内新闻事件,1938年在武汉创刊,8月即迁重庆,抗战期间坚持出版,是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。台湾学者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回忆抗战时期的“人和事”,特别说到《时与潮》:“在那个时代,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,《时与潮》是很受欢迎的刊物,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,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。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,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。”抗战胜利后,《时与潮》曾停刊,后于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。
《时与潮》以“报导时代潮流,沟通中西文化”为宗旨,实则主要从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等公开出版的杂志上,选译国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文章。金庸本人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自己在《时与潮》的这段兼职经历,只能从《时与潮》上发表的大部分的译文和编辑署名有所窥见。仅1947年11月1日,金庸就在《时与潮》半月刊第二十八卷第六期发表《苏联陆地战略的秘密》《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》《莫洛托夫的左右手》,同日,在《时与潮副刊》第八卷第五期发表译文《SVP——万能服务处》《电脑》《了解你的头发》《铝是一种新药吗?》。在《时与潮》半月刊发表译文最多的一期,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:《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》《社会主义与》《巴勒斯坦怎么分治》《法国饥馑的原因》,一口气连登四篇。
《大公报》港版复刊后,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,租用的是《新生晚报》的二楼,地址位于中环的利源东街15号,这里一切简陋,工作辛苦。金庸继续翻译电讯,担任国际新闻版的编辑,协助编辑国际新闻版。《大公报》宿舍是普通的四层旧楼,位于中环坚道赞善里8号楼,距离利源东街隔两条街,走路只需十来分钟,金庸中午吃饭,下午睡觉,晚上工作。除了新闻类的译文,他用“镛”的笔名还翻译了一部长篇自传《我怎样成为拳王——乔路易自传》,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至1949年3月16日,共47期,连载开始前,有一段小引,估计为金庸所加:“本文于十一月八日起在美国《生活画报》刊载,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,叙述他怎样从一个农奴的家庭中生长为世界闻名的拳王,其中包括许多拳击中的要诀。”
这个题目不算很难,陈文统有所准备,记熟了专用单词,答了一小时便交了卷。金庸后来回忆:“当时的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。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,就录取了,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(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)。”陈文统顺利进入《大公报》,最初也在编译组,负责翻译国外通讯社发来的英文电讯稿件,成为金庸的同事,只是他的译文太重文采,常常超出原意,大都上不了国际版的头条。当然,后来陈文统写武侠小说,笔名梁羽生,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宗师就这样结识了。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掀开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幕,推动新派武侠小说跃上历史舞台,但两人的性格与理想全然不同,金庸强调个人主义,国际化的阅读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人物内心的体悟,而梁羽生雅善辞藻,注重集体主义,这些从二人对待译文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见苗头,却都没有脱离时代给予他们的烙印。
金庸在《大公报》一直工作到1958年,在这期间,他翻译的作品除了国际电讯,主要集中在几类:其一,是长篇的新闻的报道,比如以“乐宜”为笔名翻译的美国记者贾克·贝尔登的长篇纪实《中国震撼着世界》,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0日,连载于《新晚报》,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,分上下两册,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,3个月后再版,又印一千册。他还翻译了美国《星期六晚邮报》上的《朝鲜美军被俘记》,同样在《新晚报》上分8期连载。1952年1月到6月5日,翻译了英国记者R.汤姆逊撰写的长篇报道《朝鲜血战内幕》,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。其二,是文艺评析,他以“子畅”为笔名,翻译了美国剧作家J.劳逊的《美国电影分析》86篇,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,连载于《大公报》,此外,还有《荷里活的男主角》《论〈码头风云〉》《我怎样学舞》等文章。其三,是生活情感和社科哲思,比如以“子畅”为笔名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洛亚的《幸福婚姻讲座》等。
鲁尼恩为人仗义,荡检逾闲,赌博、酗酒、吸烟、婚内出轨样样不缺,其赌品不佳,喜欢打听内幕消息下注,赛马是他写作中的主题。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馆的世界最伟大作家系列1979年收录了他的小说集《红男绿女》。富兰克林图书馆多是出版世界经典、美国经典、普利策获奖等系列丛书,早期代表了当时书籍装帧印刷艺术的天花板,成品全真皮装帧,竹节书脊,内文为无酸厚道林纸,配以精美插图,三面全金口,前后扉页真丝缎面,缎带书签;必须一订一整套,先交钱后发书,大概一月一本,读者要五到八年才能集齐整套书。在20世纪70年代,一本订价高达28美元到45美元,极为昂贵,是无数藏书者垂涎的对象。鲁尼恩能入选其中,虽不如德莱塞、海明威、威廉·福克纳有名,却足证其在美国文坛中的地位。
金庸最早翻译鲁尼恩的小说,现可考证的是短篇小说《记者之妻》,1948年9月6日开始连载,达蒙·鲁尼恩译为冷扬,译者署名白香光,这是由赵跃利《金庸笔名知多少》一文最先考证出来,后来严晓星《金庸年谱简编》也采用了这个说法。这篇小说曾引起了读者兴趣,1948年9月14日《大公报》第七版“大众顾问”栏目中,有读者来信询问:“编者先生:近日见贵报大公园刊登《记者之妻》一文,内容非常精彩,兹请问一冷扬是何国人,其生平如何?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同《记者之妻》那样差不?二白香光是谁?是先生呢还是小姐?有名的还是没名的?三这篇登完之后(因写短篇小说,大约不长吧),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?”报纸答曰:“一冷扬是美国现代最知名的幽默作家,他曾做过近二十年的警察局消息记者,对美国的下层阶级很熟悉;他的作品都是以幽默的笔调,俚俗的口语来描写黑暗社会人物的人性。二白香光是先生,他还年轻,未享盛名,但在我们看来,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,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。三这篇已登完,还会登类似的。”嗣后1948年11月23到28日,再次刊登了鲁尼恩的小说《会一会总统》,译者署名还是白香光。
金庸翻译鲁尼恩小说似不在少数,他曾以温华篆为笔名,在《新晚报》上连载了《马场经纪》《神枪大盗》《开夹万专家》《超等大脚》四篇。1956年4月,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“滑稽讽刺小说”,书名《最厉害的家伙》,封面写明“丹蒙·伦扬作”“金庸译”,这本集子收录了七篇小说,依次为:《吃饭比赛》《柠檬少爷》《记者之妻》《十二枪将》《最厉害的家伙》《超等大脚》《恋爱之王》。小说集里没有前面提到过的《圣诞老人》《会一会总统》《马场经纪》《神枪大盗》《开夹万专家》,却有《超等大脚》。可以推测,金庸翻译鲁尼恩的小说不会是只有十二篇,若仅只十二篇,似没有理由遗漏,这应是一本译著精选,更多篇章可能以不同的笔名散落在其他报纸。
比如《最厉害的家伙》这篇,能被选做书名,显示出金庸对其的喜爱。故事讲述了“我”和铁锈查理在一个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。“我”血压高了,医生却劝“我”要平静生活,否则一定会完蛋。“我”交了十元诊费后,出来碰到了铁锈查理。在“我”眼里,铁锈查理是世上最厉害的人,比如他讨厌一个人的帽子,会直接开枪打死,如果不开枪,就用刀子刺,总之这是一个极其暴力的恶棍,“他所以没有入狱,惟一的原因是他刚刚从监狱中出来,当局还没有时间想法子再把他关进去”。“我”很担心自己的血压,不想和他混在一起,但是又不敢惹他,在他的胁迫下去抢了弥敦·底特律和猪猡伊凯的赌场,还在布希米亚夜总会打了四个警察。这一晚“我”吓得血压都要爆掉,又不敢离开。铁锈查理为了表示对“我”的不离不弃,邀请“我”去他家吃早餐,让他老婆做火腿鸡蛋。“我”想他老婆的生活一定苦得不得了,没想到进了门,看到铁锈查理的老婆身材异常矮小,他老婆二话不说,拿起棒球棍就打他,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恶棍铁锈查理被老婆揍了,却说:“平平气,小嘟嘟,等一下,甜心。”“我”最终也被他老婆用棒球棍打了头,冲下楼后,铁锈查理老婆还扔了块砖头,打在“我”后脑上,肿起了一大包。第二天去看医生时,医生量了血压说:“你的血压现在已经低于正常的标准了,你看,你好好休息一晚有这样大的功效。诊费十元。”
我一直以为鲁尼恩的小说在内地没有中文译本,结果“啄木鸟杂志”公众号2022年10月14日发布了一篇翻译小说,作者正是达蒙·鲁尼恩,叫做《一个十分危险的人》,大致讲的是一个小镇来了个叫摩根·约翰逊的年轻人,因为长相凶恶,脸上有伤,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个危险的人。渐渐的镇上的人都这样传说,并且说他脸上的伤是在纽约和十个歹徒打架留下的,后来这个人数甚至上升到了二十个人,但是有一天,一个喝醉的牧羊人拿着刀威胁摩根,结果摩根转身就逃跑了,再没有回来。
从上面提到的两篇小说内容,以管窥豹,约略可以看出鲁尼恩小说的特点,这种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”的写法,类似于不停翻包袱,有些相声“三翻四抖”的感觉,语言诙谐和幽默,难怪金庸将其定名为“滑稽讽刺小说”。金庸在《最厉害的家伙》的“译者后记”特别说:“伦扬的文笔非常奇特,全部没有过去式,而俚语之多之怪,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罕有的。”金庸为了保留这个特点,在翻译过程当中使用了颇多粤语方言,比如贴士(tips,内幕消息、提示消息),温拿(winner,胜利者,赢家),契弟(骂人话,约等于混蛋),瓜直(也有写作瓜咗,死亡)等,这些语言的使用,颇能赢得香港读者的亲近感,也贴合原作。
1955年2月8日,金庸撰写的《书剑恩仇录》在其供职的《新晚报》连载,此前的1952年,金庸从《大公报》调至《新晚报》编副刊“下午茶座”栏目。《新晚报》属《大公报》旗下,最早是为了刊登报导朝鲜战争消息而成立。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香港《大公报》即公开宣布:“自本日起,遵令正式实行公元。”报头从“中华民国三十八年”改为“公元一九四九年”,明确其拥共爱国立场,一直位列香港报纸首席。当时香港报纸如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等一般不采用外国通讯社稿件,而新华社稿件来得太慢,所以就办了一份相对中立的报纸《新晚报》,便于刊登外社消息。
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风行,促进了《新晚报》的发行。当时香港地区同属阵营的报纸副刊,一般少用社会来稿,多由各报编辑提供,一来内容可靠,二来亦可在稿费上有所补贴自己的编辑。1955年底,同样具有拥共立场的《香港商报》总编辑张学孔和副刊主编李沙威找到梁羽生,希望他也为《香港商报》供稿,“但梁回复是:‘我是搞新文学的,开这个笔,只算是向报馆的一个交代,一之为甚,其可再乎!’(大意)他是不答应了,商报转约金庸上阵”。此时金庸从《新晚报》调回《大公报》当副刊编辑,李沙威就转请金庸为副刊《说月》写一部武侠小说。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共连载575期,完结时间是1956年9月5日,当时尚在连载中。金庸答应了李沙威,从1956年1月1日撰写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《碧血剑》,一直连载到当年12月31日结束,时间整整一年。这个过于巧合的时间,显然来自双方之间曾有的约定,这可能也是《碧血剑》草草收场的原因。这种做法无疑伤害了小说的整体布局,金庸后来在《碧血剑》上的修订,花费心力最多,但仍是其小说中质量不高的一部。
至于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则是金庸小说连载之后,他最早授权出版单行本的出版社。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金庸小说,主要是金庸创办《明报》前发表的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,另外一部《雪山飞狐》是否得到授权,一直有争议。坊间有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《雪山飞狐》存在,但是金庸予以否认。在1959年8月,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第十六集版权页上,有一段“作者郑重启事”:“本人所撰武侠小说,全部仅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雪山飞狐》《神雕侠侣》五种,均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,此外并无其他著作。”究竟这段文字的确是金庸声明,还是出版社自为,暂无考证,若是金庸同意的话,那么金庸可能准备将所有面世的小说都交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,彼此合作应是愉快的。
金庸对鲁尼恩小说的持续翻译,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,或者金庸当时翻译鲁尼恩小说的目的,就是在为自己创作小说进行揣摩学习。金庸在《最厉害的家伙》“译者后记”中特别夸赞鲁尼恩“是美国小说界的一个怪才,他所写的小说独树一帜,别出心裁,常有意想不到之奇”。鲁尼恩小说的戏剧性与传奇性,可以对应中国的武侠小说,鲁尼恩笔下出现的黑道人物,亦可对应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草莽。《碧血剑》中袁承志以牧童身份出场一段,不难看出受鲁尼恩小说的影响。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轻松幽默、诙谐调侃的笔调,以及对笔下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刻画,显然亦能在鲁尼恩的小说中觅到隐藏的蛛丝马迹。两人都从事报业新闻工作,叙事的节奏上也可找到相同点。具体到更深入的研究,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,能够发现更多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,也期盼更多鲁尼恩的小说的中文译本进入中国。
胡敏生记书报社也作胡敏生书报社,其实就是邝拾记书报局的副牌出版社,负责邝拾记书报局的海外发行任务,实质上“两块牌子一套人马”。邝拾记书报局出版发行金庸的武侠小说,大致从1959年5月20日《明报》创刊,《神雕侠侣》连载后一周开始。金庸初期有过“一女两嫁”的计划。《明报》1959年7月18日《神雕侠侣》第60期文末答读者问:“张明先生:《神雕侠侣》第一集的正版本正在整理中,仍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。”第二天的第61期,又有:“宝宫先生:《神雕侠侣》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,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,均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。你欲补阅前文,可就近购阅。”
邝拾记书报局与金庸的合作至1967年。邝拾记老板邝拾与金庸政治立场不合,终止合作。这里又涉及了三家出版发行机构,“出版”和“发行”有分有合。按时间顺序,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是邝拾记书报局出版、发行“一肩挑”,《鸳鸯刀》由胡敏生书报社出版发行,《倚天屠龙记》之后的几部书,由武史出版社出版、邝拾记书报局发行。武史出版社是《明报》的出版社,金庸为出版发行《武侠与历史》杂志而设立,发行还是交给邝拾记书报局。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解释金庸与邝拾记书报局、胡敏生记书报社的渊源,据此可以看出“胡敏生”不会发行伪造金庸的译作,这本书是金庸的长篇小说译作无疑。出版者野马小说杂志出版社也可从侧面证明,金庸最早想自立门户,创办的并非《明报》,而是小说杂志,计划十天一本,名字就叫做《野马》。《野马》源自《庄子》:“野马也,尘埃也,生物之息相吹也。”取其“很自由、有云雾飘渺”之意。金庸一直很尊崇英国哲学家罗素自由、反战的理念,在他看来,“野马”象征一种自由的精神。1959年3月,金庸和沈宝新还将这个名字进行了注册,只是后来听从报贩的建议,改为报纸。办小说杂志的愿望,金庸始终没有熄灭,1962年8月15日,他推出了小说杂志《野马》,出版至1969年停刊。
《蒙梭罗夫人》有真实的历史背景,有权力和背叛,有爱情和阴谋,有嫉妒,也有贪婪,有刀光剑影的决斗,也有花前月下的浪漫,有慷慨的英雄,也有阴险的小人……可以说,你能想到传奇小说里一切想要的元素,这本书全都写到了。金庸选择翻译《蒙梭罗夫人》的原因可能亦在于此。《蒙梭罗夫人》的故事一条主线为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(即《玛戈王后》中的阿朗松公爵,受封安茹采地后称安茹公爵)窥伺王位,暗中针对亨利三世开展阴谋活动;另一条主线为安茹公爵手下勇士比西与狄安娜的爱情,狄安娜又被王家犬猎队队长蒙梭罗欺骗,成为了他的夫人,同时,安茹公爵也觊觎狄安娜的美貌,形成了四角恋,贯穿于整本书中。
诚如金庸在“引言”中所说“摘录译出”,这种译法似乎在模仿伍光建翻译的《侠隐记》,删节某些段落,加快叙事节奏,却又不伤害故事的完整和精彩。翻译语言上,金庸也明显在致敬伍光建的译本语言。如《侠隐记》中主人公达特安(今译达达尼昂)初遇颇图斯(今译波尔多斯):“看见中间一群人里,有一个身躯壮大的火枪手:模样十分骄蹇,身上亦不着号衣,只穿一件天蓝夹衫,肩上挂了绣金带子,外罩红绒大衣,胸前露出那绣金带子,挂了一把大剑。这人值班才下来,故作咳嗽之状,说是受了点风,故披上红绒大衣;一面大模大样的在那里说话,一面拿手来捋须。”不是文言文,也不似现代白话文的语言。茅盾在谈伍光建所译《侠隐记》,特别说:“伍光建的白话译文,既不同于旧小说(远之如‘三言’、‘二拍’,近之则如《官场现形记》等)的文字,也不同于‘五四’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,它别创一格,朴素而又风趣。”
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,没有互联网,新闻消息主要依靠世界各地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,要想及时报道国外的消息,直接翻看国外的报纸杂志是最便捷的途径。曾有读者来信询问《明报》的信息来源,金庸回复说:“买来的。”《明报》成立初期,金庸经济拮据,无法订阅诸多的报刊,他就每天花时间去报摊和书店翻查。当时他住在港岛,报馆办公室在九龙,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,他曾说:“九龙尖沙咀码头前,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,美国的《》《先驱论坛报》,英国的《》《卫报》《每日电讯报》《每日快报》《每日邮报》,西德的《佛兰克福日报》《汉堡日报》,日本的《朝日新闻》《每日新闻》《读卖新闻》,以及泰国的《日报》,菲律宾的《马尼拉时报》,新加坡的《海峡时报》等等都有。普通都是一元一份。如果每种都订下来,当然太不经济,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。我经常去翻翻,看到有合用的资料,就花一元买一份。”
翻译作为金庸重要的工作之一,几乎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。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,金庸访问厦门、泉州,他与厦大教授李晓红对谈时回忆:“当年我在《大公报》还学做翻译,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,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,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。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,怎么就不好了,我至今还能记得。”金庸口中的翻译老师,就是当年招聘他进入《大公报》工作的翻译主任杨历樵,被同仁呼为“杨老令公”。
“怎么翻译比较好,怎么就不好了”关乎翻译中“词义确定”和“表达得体”两大主题,金庸的回忆,其实切中了翻译的重点。关于金庸的生平,资料愈加丰富,但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,金庸一生对自己的翻译生涯谈得不多,远远少于他针对政治、历史、文学、新闻学发表的言论,然而,金庸的翻译工作确实占据了他生命中的绝大比重。对于翻译的标准,金庸没有具体阐释过,他在《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〈心经〉》一文中曾称赞:“实在译得既简洁,又明确。”可能就是他对翻译境界的认同。金庸写“三剑楼随笔”时,在《谈谜语》一文中说:
欧美人用拼音文字,字谜就远不如我国的巧妙,英文中的字谜大抵在“同音”与“双义”两点上着眼。前者如“王老五为什么总是对的?答: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小姐。”(never miss taken,音同never mistaken,从来不错。)后者如“律师为什么如同啄木鸟?答:因为他们的Bill都很长。”(Bill既有账单的意思,也有鸟嘴的意思。)还有一个开律师玩笑的谜语:“为什么律师像失眠者?答:因为他们都是这边lie一下,翻过来那边又lie一下。”(在英文中,lie这字既是睡卧,又是说谎。)
信手拈来,却又举重若轻。翻译为金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养分,他的翻译文字又深受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。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深刻表现人性,在金庸的眼中:“人的性格和感情,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。”对人物进行观察、分析和描写,是作家的习惯和看待人与事的切口,所以在金庸的翻译文本中,可以发现他喜欢从人的角度出发,将人物植入到具体的环境,通过人物的行为来书写评判。翻译的基本原则是“信达雅”,对金庸而言,实用是第一法则,他在不同语种中切换,翻译更像是他手中重要的观察利器,充溢着个人的思索与体悟。在金庸的小说和文章中,东西纵横,古今对照,其中五花八门、千奇百怪的广博知识,无疑是“译入”和“译出”的具体体现。
《明报月刊》的前总编胡菊人认为,金庸的文章是香港的第一流文章,“第一”太主观,而第一流怎样都说得过去。这和金庸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分不开。他的用功是罕见的,很多事情他听到批评不做回应,但他会暗暗用力,就像他以八十高龄一定要去剑桥大学读个博士回来,还要用英文去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,倪匡笑话他“滑稽”,他也不理。以“翻译”回溯金庸的半生,正如《明报月刊》现任总编潘耀明所言,博士很多,但金庸只有一个。文字的江湖中,将永远留有金庸的名字。